【文化芊言】刘芊:孔子会喜欢贝多芬吗?
相关附件:
刘芊,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副教授 研究领域为传统文化与管理、跨文化管理
美国音乐教育家雷默(Bennett Reimer)把对艺术的不同认识分为“绝对主义”和“思辨主义”两大类。根据他的说法,绝对主义者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作品本身;思辨主义者则认为艺术作品的意义和价值存在于其本身之外:音乐在多大程度上使你联想到一种非音乐的体验,它就在多大程度上是一部成功的音乐作品。反之,如果一部作品只是听着美,没有什么音乐之外的意义那就是颓废和无用的。换句话说,“艺”是为载“道”,纯粹的艺术是不可取的。儒家的乐教思想,是为了礼的教化,不把乐作为单纯的审美对象,那么应该是典型的思辨主义了。可事情似乎没有这么简单。我们先看看孔子是如何进行乐教的。
从因材施教的角度来说,只有具备音乐天赋的,才应教之以乐。朱熹也说“盖终日以声音养其情性,亦需理会得乐方能听。”听尚如此,演奏就更难了。如果说“身通六艺”的七十二贤人得乐教之传,那么孔门三千弟子应该并非都是乐之教的对象。是否可以说,乐之教并非孔门必修,而是只有具备一定自身条件与素养的人才能学习的特殊科目?从史料中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。或许从一句“游于艺”中我们多少可以体会出一些包括乐在内的技艺属于“选修课”的意思。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,孔门弟子的乐之修养是参差不齐的。志在“浴乎沂,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曾皙,在孔子与弟子门们谈话时独自一旁鼓瑟(《论语•先进》),可见其与音乐的关系近于他人。而孔武直率的子路(仲由)虽然也鼓瑟,却被孔子奚落:“由之瑟,奚为于丘之门。”以至于门人不敬子路,孔子才又改口,以挽回子路的面子:“由也,升堂矣,未入于室也。”由此留下一个“登堂入室”的成语。后来据此敷衍出孔子批评子路鼓瑟有北鄙之声,应是借题发挥。子路之瑟不被孔子赏识,恐怕只是因为子路缺乏音乐天分。以其一介赳赳武夫,“援戚而舞”(《孔子家语》)来抒发情感显然要比弄弦鼓瑟更为痛快传神。
从孔子的教育一向注重个体的差异,具有很强针对性来说,我们推测孔子的乐教也是因材而施,恐怕不会离事实太远。总之,孔子除了自己弦歌不辍以外,其乐教应该是个体性的和非强制性的。
孔子以“仁”来诠释作为外在行为规范的“礼”。礼乐不能是徒具形式的外在修饰,而应是内在德行的涵养与表现:“人而不仁,如礼何?人而不仁,如乐何?”(《论语•八佾》)孔子之乐,如春风化雨,由内而外自然地改变人,让作为个体的人在和谐音乐的潜移默化中达到身心、乃至社会的和谐,使道德规范内化到人的生命中,令人不仅“好之”,还要“乐之”,以至达到一种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自由境界。
在孔子这里,乐教除了有其政治诉求之外,本质上是个人修养的完善。这为礼乐价值的挖掘打开了广阔的空间。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循着这个路子探索个人境界的提升方法。如北大楼宇烈教授所倡导的“由艺臻道”就是这样一种主张与实践。给乐赋予道德和审美的精神内涵,使其从国子普遍学习的一般技艺上升为自我完善的最高功夫,可以说是孔子对乐教的最大贡献。作为艺术上“思辨主义”的代表,托尔斯泰非常注重艺术的道德问题。他认为“音乐的最佳范例是进行曲和舞曲,他们接近要有鲜明易懂的信息的条件。”我们对照雅乐重节奏,追求铿锵蹈厉,进退得齐,不难发现其中的相通之处。托尔斯泰进而主张“好的情感是那些引起人走向基督教的博爱的情感”,因此他认为“贝多芬或许是最贫乏的作曲家了,他的最弱的作品就是《第九交响乐》”。然而徐复观却认为,“假使能使孔子与贝多芬(Beethoven)相遇,一定会相视而笑,莫逆于心的。”同样作为“思辨主义”音乐思想的代表,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不同?这是因为儒家乐教思想的根源中包含着从感性出发,将人的情操引向崇高的机制,而没有把音乐与道德割裂或对立起来。
我们抛开礼乐制度,单从孔子的乐教实践来看,不难发现其中的独特价值。孔子的教育目的在于“成人”,教育的方法针对个人,教育的形式注重以情感为出发点,将人的思想品格引入向上一路。这其中没有强制的暴力,没有生硬的灌输,循循善诱,发挥乐之潜移默化的功能,使人浑然无觉地提升自己的人格,在审美的最高境界中与道德的最高境界相感通。因此孔子主张“兴于诗,立于礼,成于乐。”徐复观说:“孔门‘为人生而艺术’的最高意境,可以通过各种乐器、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出来;最重要的一点,只存乎一个作曲者、演奏者的德性,亦即他的艺术精神所能上透到的层次。甚至可以这样说,从‘无声之乐’的意义推下来,也可以由俗乐、胡乐、今日西洋的和声音乐,提升到孔子所要求的音乐境界,即是仁美合一的境界。” 这就是他认为孔子与贝多芬可相通的原因。当然,如果站在后世日趋保守的立场上,将“郑卫之音”的标签随意地粘贴,那必然在音乐的问题上成为托尔斯泰的同道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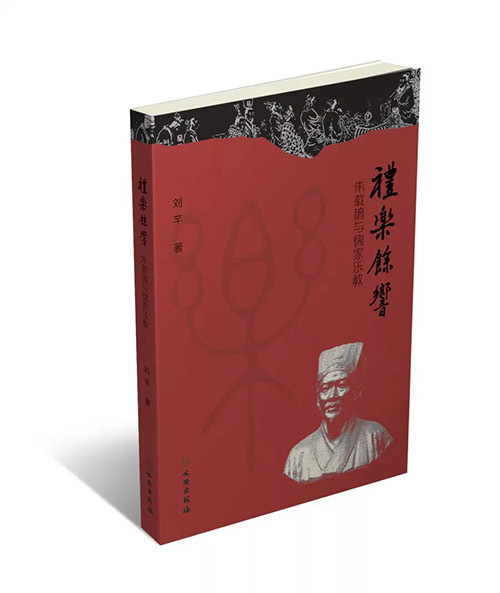
(本文部分内容取材于作者新书《礼乐余响——朱载堉与儒家乐教》)



.png)




